吴锦牵,男,1992年10月生。独生子。有苯丙酮尿症。1999—2000年在云南省昆明市一所康复学校接受基本生活训练。2000—2004年寄托在私人家里。2006—2007年在广东省名扬语言训练中心接受训练。2008—2010年初,在广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托养。2010—2014年,在昆明一家养老院、昆明市儿童福利院生活。2014年离开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后,一直在家安养。
我们家里的布置看起来不像一个困难家庭,事实上呢,我们是一个困境家庭。我跟他爸爸两个大学毕业生,算是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定的职位和社会地位,收入也比较稳定,为什么我们会陷入到困境当中呢?就是因为我们儿子。
锦牵小时候,周围人都说长得像小老外,我和他一块儿上街,别人还以为我旁边是一个外国人呢。
他从小吃母乳。孩子8个月大的时候,到妇幼保健院体检,一个年轻的男医生对我说孩子好像脑子有毛病,被我骂了一顿,医生不敢再出声。9-10个月的时候,锦牵开始抽筋,每天基本是早晚各一次,一抽筋就会“点头哈腰”。锦牵的状况持续到1岁零9个月,我们夫妻二人带他到北京中日人民友好医院确诊为苯丙酮尿症后,医生指导我们在饮食上控制锦牵苯丙氨酸摄入量,他的症状才逐渐消失。只是这时候锦牵体内的苯丙氨酸在血液里的浓度已经很高,由于先天缺乏苯丙氨酸分解酶,导致他大脑神经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神经已经受损,而且不可逆转了。无论如何,这是无法挽回的遗憾了。
我从2014年开始带锦牵,越带越有内疚感,觉得是我谋杀了他,因为锦牵吃母乳吃到了一岁零四个月,母乳是高蛋白啊,他分解不了,牛奶母乳对他来说是一种毒药。
我和孩子的爸爸都是有这方面基因的隐形携带者,是基因缺陷的人。我们两个如果只有一方有这种情况,孩子不会有问题;我们两个碰到一起,孩子出问题的可能性只有四分之一,也被我们碰到了。这只能说是一种巧合。一开始这个巧合落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接受的。于大夫还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告诉我们作为高学历的人,回去之后一定要向社会宣传:第一,苯丙酮尿症是一个遗传疾病;第二,它是可以控制的。母体怀孕三个月的时候一定要穿刺抽羊水化验排除这个可能性。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家长可以选择要这个孩子或者不要,要的话要考虑好未来的情况,而且在孩子出生之后,要抽脚后跟上的一滴血进行化验。现在很多罕见遗传病都可以这样化验出来。于大夫还说,苯丙酮尿症可以早知道早介入。
锦牵是比较失败的案例,因为我们没有一开始就介入,后来也只能进行控制。现在昆明慧灵里面有一个28岁的姑娘,也是苯丙酮尿症患者,她的基本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可以自己坐车到慧灵,可以自己发短信、自己吃饭,只是不喜欢与人交流。
国家规定九年义务教育,但是能有幸进入到特殊教育学校的每年只有100多人。云南省现在有33.7万智力残障人士,光昆明市就11万,有幸进入学校进行技能训练的,能学会拿着钱买菜、会找零钱、会炒菜,和人交往没有太多障碍。等到他们16岁之后,学校就不接收了,这些孩子就回到家庭由爷爷奶奶带,或爸爸妈妈其中一个人带,大部分都是妈妈带。如果家庭不是特别配合,孩子在家3个月,在学校学的技能就退化了。锦牵就是这种情况,我到现在才理解。
他在广州慧灵度过了非常开心快乐的两年,2008年到2010年2月。
慧灵是一家非常好的公益机构。公益机构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肯定会少收费,当时我们把锦牵送过去是1500块钱,而且我们半年才去看他一次。广州慧灵当时硬性规定,家长至少要半年来看孩子一次,因为孩子们是有感情需求的。老师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孩子不懂感情。”有些孩子的家长就想着过年的时候多给点钱,让慧灵帮着带孩子。慧灵是绝对不干的。每个孩子都需要父母的爱。
他也有很大的情感需求,需要进行情感的宣泄。
养老机构,必须要有专业的第三方监管,否则很可能有虐待现象。
有人问过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把锦牵遗弃掉,我说是因为我们这个家庭有爱有责任心,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但是很多家庭并不愿意承担的。
照顾孩子是一个有苦有累但是很快乐的事,让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幸福感,这是以前拼命工作没有带来的东西。我们每天要带他去散步三次,鞋已经磨坏了三双了,带他逛了好多公园、去了好多地方、看了很多事,也相当于我们在锻炼身体。锦牵出去散步很开心,看他开心快乐我们当然也很快乐。我认识到了带孩子的重要性。父母的陪伴其实对孩子是最好的。亲戚朋友们看到锦牵之后都说他变化很大,比以前懂事很多。
现在我做一些家长的工作,都会告诉他们只有陪伴孩子才是最好的解药,不要去丢包袱,不要把孩子丢给那些机构里面就撒手不管。
锦牵很喜欢散步,就是纯散步,出去他总是牵着我们的手散步。
我从来没有怕被别人嘲笑的心理,很愿意带锦牵到各种场合,游泳、逛街、郊游、交际等等都愿意带上他。
我很鼓励他去交一些异性朋友。
心智障碍人群的性需求,是很严肃的问题,是需要探讨的。我给锦牵洗澡、换尿片,我觉得很自然,但是我嫂子,比我要年轻一些,有点顾忌这些,告诉我她可以领锦牵散步,但是不会给他换尿片的。
在台湾、香港和国外的不少地方,会有专门满足残疾人性需求的志愿者。我们慧灵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慧灵总部请了老师过来对这些家长进行过一些关于大龄心智障碍者的性需求的讲座,提到在澳大利亚有一个为残疾人服务的性从业者,是一个女大学生。但在中国,很多人是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的,如果对智障者家庭做这方面调研,可能不少家庭不愿意去谈。
台湾有鼓励智力障碍的人群在一起生活,政府给他们提供廉租房,让他们能够独立生活。这主要是政府支持很到位,同时有社工上门来帮助。这正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如果这两方面的支持不到位,就算鼓励智障人士正常的交往交际,组建家庭也会困难重重。
因为他是重度的,所以说婚姻我们没有怎么考虑过,只希望他在同类群体中能交到朋友,多一些空间,多一点快乐就好。
医生说在母体做穿刺并不是百分之百能查出来先天性遗传病,只有等到孩子出生后亲自验血才能准确检测出来。
每个人作为个体来讲,必须要承受自己面对的苦难,也要去超越这种苦难。超越苦难是要有一些东西能触动你,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件事,也可能是一种东西让自己打开心结;否则很可能走不出来。
所有这些家庭都是先哭过之后开始慢慢接受孩子。心结难解的漫漫长路是每个这种家庭的必经之路。前面说到,锦牵1岁9个月时去北京看病,我在于大夫诊室里发现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家庭,这次触动让我的心结解开了一半。还有一次是带他去爷爷的老家玩,爷爷有一个亲妹妹在那边,对我们非常好。那边有一个云龙桥,是铁索桥,下面是澜沧江,江水湍急。有一天,锦牵早早起来沿着江边小路散步,往云龙桥方向走,我在后面跟着他,想看看他到底去哪里。锦牵喜欢听声音,听到江水的声音就往前走,走到江边拉着铁栏杆听江水的声音,我没打扰他,远远地坐在一块石头上看着他。那一刻,我的心结完全打开了:孩子是上帝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来带我欣赏青青的山、静静的路、湍急的江水,我一定要珍惜我的孩子。
救助这类孩子要花很多的金钱,社会应该有个救助体系,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对于罕见病的救助还没有很好的支持力度。
更多的帮助来自于家庭和家族。我们两边的亲戚都很好,知道孩子这个情况之后,都凑钱帮我们。家里面人可以说对他有一种溺爱。家族的支持、家族的爱是我们走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爸爸从来不认为儿子是有病的,一直说孩子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他是苯丙酮尿症患者,这个病从理论上来讲大概只能活十八、九岁。对于锦牵来说,他的生命已经算一个奇迹了,周围人都觉得我们很伟大。他的20岁生日,还有昨天25岁生日,我们都进行了庆祝。我感觉我们家现在的状态是最好最圆满的,也是最快乐最幸福的,虽然也会累一点、苦一点。
我们这个家庭属于老残一体的家庭,我们的年纪也会越来越大越来越老。
我和爸爸都不敢有事、不敢病、不敢死。
这种孩子是拥有生命权的,他们应该受到尊重,不应该被排除在国家的救助体系之外。从生命规划来讲,从他们出生那一刻,就要形成一个支持网:孩子出生前,应该有医疗机构告诉孩子的妈妈怀的孩子有什么问题,自己决定要不要孩子;要了,政府肯定要给一些支持,一是经济上的,二是政策上的,三是教育上的;16岁之后,要有一些社会机构来接纳他们,直到他们的生命历程结束。像我的孩子锦牵,明摆着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到那一刻时,我们这些困境家庭的父母的心理安慰,或者叫临终关怀谁来做呢?
国家应该有社区服务机构,在社区有社工或者助残的机构定期上门到困难家庭或独居家庭,至少每天打个电话,问一下家庭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如果不需要,就不用过来了,如果有需要,就过来,这是我的梦想。必须要有这种专业的助残机构,把每个社区的困难家庭或者双老家庭全覆盖;而且,上门服务的社工需要有资质,要经过训练,服务也要有监督。
我从2013年开始做智协工作从小爱到大爱,除了关心锦牵以外,也在关心他们这样一个群体,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关心、支持他们。现在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支持体系还没有做好。我一个人看到这一点不行,要让更多人看到。
云南心智障碍的人挺多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些障碍,所以要平等对待每一个生命,包容每一个生命。
我们参加过特奥活动,也给了我很大的感触。我是在做智协工作时了解到特奥魅力的。我们家两口子年轻时候都算体育健将,如果早在20多年前我们知道特奥运动,锦牵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很可能会是一个优秀的特奥运动员,因为毕竟有基因在这儿嘛。后来我了解到国际特奥运动会甚至可以专门为一类孩子设立一个项目,比如说锦牵喜欢游泳,就可以专门为他这类喜欢游泳的孩子设一个游泳项目,所以我觉得特奥特别人性化。这么好的活动需要普及到这类家庭和孩子身上,让所有的家庭都可以来参加。
最适合他们的就是体育运动和音乐,不仅能让他感受到快乐,而且会增强他的社会交际交往能力。遗憾的是,大型的特奥活动在云南还是空白,我们往往只是选几个种子选手去参加比赛,是去拿奖牌的,覆盖面很广的联谊活动很少。那次去成都,发现四川有专门的特奥运动场,云南没有。另外,云南特奥运动的教练太少了,只有几个特教学校的体育老师。从成都回来之后,我给云南省残联写了建议。
很多这样的家庭中,夫妻会有一方逃避责任,选择离婚,把孩子留给另一方。我和锦牵爸爸也曾经为生活所迫,想过下海经商,也曾经为孩子吵过、闹过离婚,后来我们体会到生活就是不断的妥协,两个人逐渐取得共识,齐心协力互相鼓励,共同照顾锦牵,虽苦犹甜,也收获了和谐温馨快乐的家庭氛围。
我被锦牵困住,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很少。不过,在陪伴锦牵的辛苦中,我也感受到许多以前没有感受过的快乐:是锦牵带我去逛公园,欣赏景色;陪伴锦牵看电视、听音乐,让我放慢了生活的脚步,去审视自己的内心,从而知道什么东西是重要的。锦牵的喜怒哀乐也是我的喜怒哀乐,总体上说,一天当中锦牵高兴和快乐的时间远远多于发怒的时间,所以我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感和幸福感。
只要简单快乐,像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吴锦牵父亲口述
1994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领养了普洱市景东县的一个孤儿,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小女孩,《春城晚报》的记者觉得我们这样的家庭还领养别的孩子,就做了报道,把我们家给宣传出去了。其实我和周老师的目的是让云南省有锦牵这样小孩的家庭,能通过我们知道在哪儿可以求医问药、小孩需要吃什么东西。因为当时好多有这个病的家庭不知道可以去哪里医治。后来云南这边一些这类家长打电话或者直接带着孩子跑到我们单位找我们,问这些小孩儿要吃什么药、去哪儿买,我们帮他们解释这个病的情况,把我们知道的信息都告诉他们。他们也都很痛苦,承受能力可能比我们低一点。在帮助和疏导他们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地走了出来。再加上,我的老岳母去算命,说是前世我们欠了锦牵一条命,这一世我们要还锦牵。老人家说:“这就是命吧!”这个也有助于我们接受现实。
不论怎么说,一家三口能够在一起我就很满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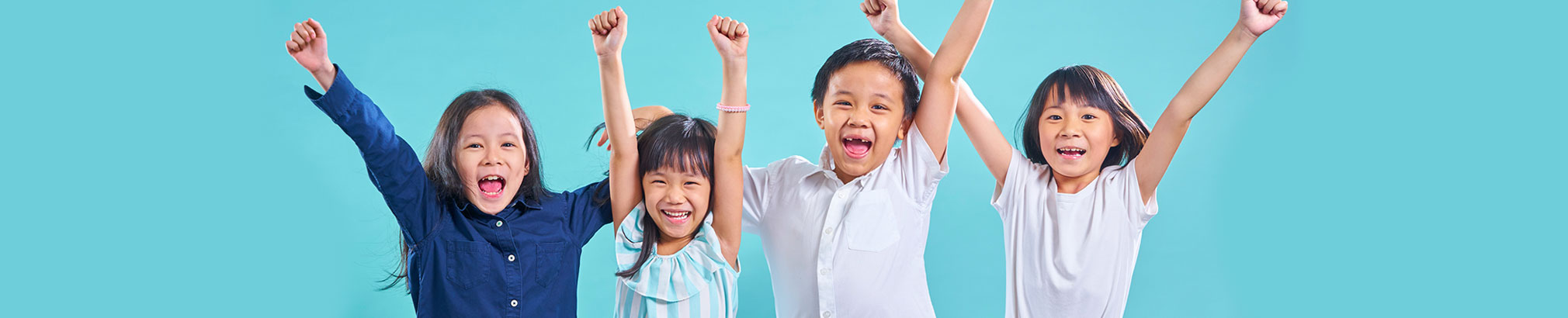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702007458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70200745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