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潇,男,1989年生。脑瘫,青春期后出现精神分裂现象。1998—2004年一直在各民办特殊儿童教育机构进行各种康复训练。2004年至今在陕西省西安慧心阳光家园学习。
我1964年的。1988年结的婚,1989年就生的这个孩子。
包括婚前检查、生孩子之前的检查,都进行过了,都没有异常。但孕期我窒息过。是顺产,头先出来的,也没有说头大出不来要用产钳啥的,是给我做了产道侧切。孩子生下来以后,大夫没说有什么不好的。孩子头发黑黑的,哭呀啥的都正常。生下40来天的时候吧,儿童医院派人来家里做保健,也没发现娃有啥问题。他吃奶也一直很正常。只是在我印象里,他婴儿期一直跟人没有对视,叫他的时候没反应。
到一岁一、两个月了吧,黄潇还是没有翻、坐、爬,我们就说到妇幼保健院去查一下。去了以后,那个医生很有经验地问我:“他吃谁的奶?”我说:“吃我的。”医生问我:“认人不?”我说:“不认人,这个孩子谁抱他都行。”医生有点怀疑他是脑瘫。正常孩子如果一直吃的是母乳,肯定是早早地就粘妈妈了,但我的孩子没有。
妇幼保健院的医生那样说了以后,我们又到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找了我妹妹的同学认识的一个大夫——王大夫,给黄潇做了CT,结果孩子大脑发育明显不好。医生当时没有直接跟我说,是回避过我,给我妹说:“给你姐说让她放弃这个孩子吧!”因为如果是大脑有问题,治疗一般没有多大效果。
你说我怎么放弃?根本就没办法放弃。我一直就想着他只是发育不好,就一直努力、努力。那些年,我们就想着孩子是有病嘛,就看病、吃药、打针。
在孩子8、9岁之前,一直都在治疗。比如,在报纸上看到哪个地方有什么做脑子康复的,或者有什么药,就去尝试。反正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孩子也是把罪都受了,长期吃中药、扎针……!
从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开始,我就没去上班了,一直带他。
我最大的失误是太大包大揽了,一个人把孩子的事都揽了下来,不仅自己累,还不能使孩子他爸体会到我的累。我给现在的年轻人说:“婚姻中,对孩子的事、家里的事,一定不要一个人大包大揽,要让另一个人参与进来分担!”
我儿子9岁左右,也就是1998年,我才知道北京有个“心心雨”在做智力障碍孩子的康复训练,我开始动心:是不是可以在康复训练这一块给孩子做一做?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西安雁塔区幼儿园有几个家长在做这个,就去找,就把孩子送到那儿。那个时候好像是100多块钱一个月。我们几个家长一起,一边自己学习,一边培训孩子,效果蛮不错的。
1999年,我们三个,就是最初在雁塔区幼儿园办这个班的那个苏老师、现在“心心特教中心”的张晓强老师、我,在三爻村租了民房,继续雇陈老师,办了一个幼儿园,我给起的名字——心心幼儿园。
最初的一年多我们办得不错,但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三个人理念不一样,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大约2001年我和苏老师就退出了,张晓强一个人办。现在“心心”还在办,就是“心心特教中心”。当时收的是三岁到十五六岁之间的。因为孩子在三岁以前,还没办法确诊是不是特殊儿童。
2001年左右,我从心心幼儿园出来以后,碰见了张涛老师,她儿子是自闭症。张涛老师的理念跟我挺一致的。2002年,我就和张涛老师投资创办了“拉拉手特殊教育中心”。最初,拉拉手特殊教育中心是按家长活动中心做的。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些孩子的康复训练主要在于家长。就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家长的观念比较超前了,就能带动孩子,家长坚持了,孩子才能坚持;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2003、2004那几年,我们拉拉手特教中心的训练效果特别好。很多孩子来的时候没有语言,或者有各种行为问题,我们就有针对性地通过对接球、走平衡木、匍匐前进、手绕圆等运动来训练他们。那些运动都挺苦的,对孩子们来说就跟我们现在练瑜珈一样,难度很大。但是,确实有效,孩子们长进很大,家长也看到了希望。
回想起来,1999-2009年,办“心心幼儿园”和“拉拉手特殊教育中心”很有成就感,但也很辛苦。
2009年的时候,西安已经有十几家特殊教育的机构了,再加上对专业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教育学专业的学生都涌现出来,可以参与进来了,我就感觉到我这种非专业的该回到我的位置了,所以2009年我退出了。张涛老师至今在做“拉拉手”。
2004年的时候,我把黄潇送到西安慧灵了。一是他已经十四、五岁了,长得又高,“拉拉手”的老师弄不动他了。二是我在“拉拉手”管后勤,琐碎繁杂,成天忙得很,管不上他。三是我想让他在慧灵过一种新生活,锻炼他的生活能力。
西安慧灵非常好的一点是社区化服务,白天孩子们在日间服务中心,16:30回住的地方,住是在单元房里面,一套房里住6个孩子、一个家庭妈妈、一个助教老师,模拟的是家庭式的生活。家庭妈妈负责做早饭、晚饭,打扫卫生、收拾,孩子们回来后陪孩子们。
我现在尽量让他做一些事,简单的家务都让他做。比如说扫地、叠被子、拖地、洗自己的裤头和袜子,做得怎么样不说,就要让他知道怎么做。我看重的是他做事的过程,他去做事了,就会少一些对家人的不断要求。他一做事,注意力就会转移一些。
有这样孩子的家庭发生变故的非常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担这样的责任,有些人承担不了就逃避。如果社会的保障好一些,这些家庭的负担不那么重了,那么这些家庭就可能矛盾少一些,和谐一点。我们这些家长里面,有些本来是大学老师、法官、银行高管,因为要照顾孩子,就把工作辞掉了,放弃了很多。没有了工作,家里的收入少一份,矛盾自然多一些。
我的婚姻发生变故,我也有责任,我顾了孩子,没顾上经营夫妻感情。但我顾不了!办学校的时候,那么多事要做,回到家孩子还是得我管,我哪里有多余的精力?就算回家了有老人能帮我管一下孩子,我哪有心情去谈情说爱?面对这样一个孩子,你心根本就闲不下来。
这类孩子享受不到9年义务教育,是家长自己掏钱给孩子做康复,还要花钱到处给孩子看病、经常买药。而且,有这样一个孩子,夫妻两个中的一个就得放弃工作专门照顾孩子,靠另一个人工作养活全家。照顾这样一个孩子已经让人筋疲力尽,哪有精力去再养一个?更何况,生二胎如果还是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即使第二个孩子是正常的,会不会从遗传的角度影响到第二个孩子以后的婚姻和生育?现在医学上好多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诊断。
我的朋友们担心我老了以后,我和黄潇怎么办。其实我不担心。担心又能怎么样?我只要把现在做好就行了。生命真的就是体验,体验自己走的那条路上的东西。
我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喜欢静下心来“悟”,不断地反思。带这样的孩子,父母太重要了。老师毕竟没有养育过这样的孩子,而父母是一点一点把孩子带大的,肯定比老师对孩子的了解多;再一个,老师没有父母和孩子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关系,不可能非常耐心地疏导孩子,老师如果情绪不好,对孩子可能会比较武断。家长必须自己用心地去观察孩子,尽到一个家长对孩子该尽的责任。
从2010年以来,我们有几个家长一直在为这些孩子的人权奔走。我会定期带一些家长去残联、政府沟通。政府办学校也好、办阳光机构也好,是为了改善孩子们的能力,让他们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能做一些事情,尽量让他们接近正常。但是,这些孩子一般不可能变成正常孩子。那么,等我们做父母的百年以后,这些孩子怎么办?就算我们能给孩子留很多财产,他们也没有能力支配。谁来监管我们留给孩子的财产能有效地用到他们身上?怎样才能保证我们现在的很多政策,比如残疾人的养老、生活保障、护理补贴等,在家长去世以后,能继续落实到这些孩子身上?再一个,9年义务教育,这种残疾孩子怎样能享受上,是融合教育还是小班制?怎样保证这些孩子也享受到义务教育的权利?……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些家长还活着的时候,能看到国家有一系列政策与行动,使这些孩子小时候有幼儿园上、有学上,让家长能安心地工作;他们生病了,能有医保卡去看病;他们就不了业,国家能有就业保障金;到这些孩子该工作的年龄,他们的保险、养老金这些,国家该帮他们交多少、家长该给交多少,都能明确规定,保证他们老了的时候,能像我们拿到退休金一样,拿到保证他们基本生活的钱。
我喜欢“融合”这个词。为啥?现在我们这种孩子出去玩,往往引起围观,正常人觉得新奇。有融合,就不会了,因为如果正常的孩子和这些孩子从小就在一个学校里,从小就在帮助这些孩子,不仅对正常孩子心灵的成长有帮助,而且他们从小就见过这样的人,就会以很平和的心态对待这样的人。现在的封闭,把两种人隔绝开来,很不好。融合教育也是文明教育,需要赶快普遍做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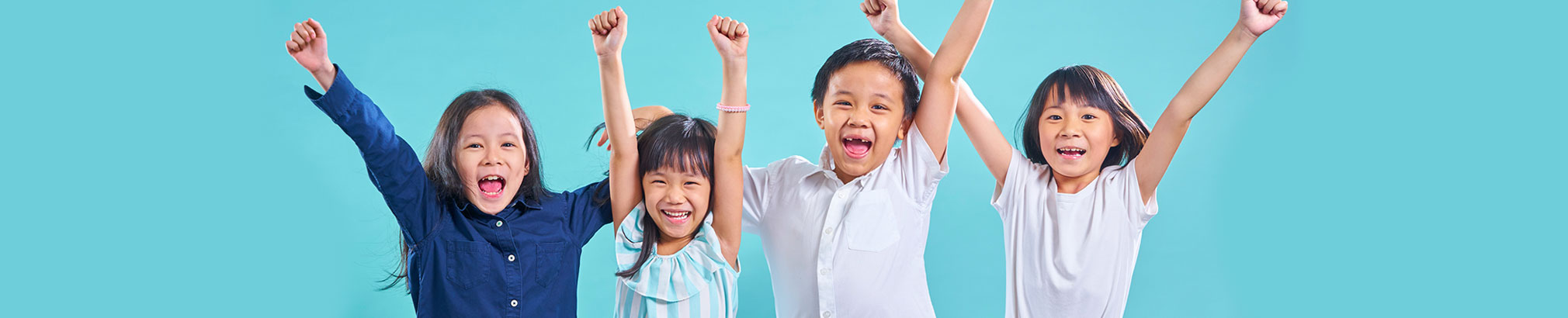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702007458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70200745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