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培钧,男,90后,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2010年高考结束,在上海世博会“生命阳光馆”第一次参加志愿服务。2015年,作为中美交流北京大学团队负责人,首次以特奥青年领袖和志愿者身份,参加世界特奥运动会社会影响力峰会,力求从政策层面上推动特奥发展并与他国青年领袖进行交流。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多次参加北京大学和培智学校的特奥活动,为特殊人群提供志愿服务。
小时候,父母经常给我讲故事,举一些例子,教导我助人为乐的精神,告诉我“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父亲经常会对我说:“就算你是小朋友,也应该有担当。当年送鸡毛信[1]的小孩,才几岁啊!在那个年代,很多小孩很小就开始参与抗日活动了。” 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我的母亲是一名医生,他们的职业和一些观念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同时,通过一些电视报道,我了解到很多英雄人物,所以这颗种子从小就开始在我的内心种下了,然后慢慢发芽长大。我十八岁刚成年,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我就去了上海世博会,成为“小白菜”[2]。同年,在广州亚运会做完志愿者后,紧接着做了广州亚残运会的志愿者等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从事志愿服务。
2015年,作为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成果,中美特奥交流活动的序幕被拉开。我又很有幸被北大选中,当时我作为十个团队成员的领队leader,跟对方美国的UCLA,就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特奥方面的交流。除了中美交流活动外,我们还参加了全球性的社会影响力峰会,当时是北大出十个学生,上外附中出十个学生,UCLA出十个学生,加州的一所高中出十个学生,当然还有世界各地的代表,不过有些国家只有两三个代表,甚至有些国家只有一个代表。当时中国的规模算是最大的,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地去接触国际性的特奥活动。
这次特奥活动与传统的为特奥运动员提供服务有所区别,我们并没有直接对特奥运动员进行服务,我们是去进行中美交流。这个交流主要是从推动特奥的政策层面上进行交流,没有真正地像赛场上的志愿者一样,一对一的进行服务。在中美交流中,我们主要负责两方面,一是我们代表之间从政策层面上进行交流;另外一个是讨论如何更好地帮助特奥运动员参加体育活动。我们当时有一个报告展示,展示我们本国或本校将来要做的一个计划,我们带着计划去跟各个国家的代表进行交流。具体来说,这个报告是我们团队共同形成的,是关于我们怎么样才能通过高校的平台,帮助特奥运动员更好地融入社会,或者跟高校进行链接,去服务他们。
我特别感谢特奥给我们机会参加交流活动。去特奥世界运动会,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USC[3],看了一场游泳比赛。当时我发现,不管是运动员得了第一名,还是倒数第一名,每一个出场和到达终点的运动员,都能赢得满场的掌声,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奥运会这些竞技比赛,比较崇尚名次,包括我自己也参加过竞技体育,我深知其中的感觉。但特奥注重的是你参与的过程,你勇于站出来参加比赛,这已经是特奥运动员的一个成功,所以当时看到游泳赛场的这一幕时是非常震撼的。
还有一点,我觉得在那会场上虽然有好几百人,但是我们真的不会去把谁分成是代表,谁是特奥运动员,没有去区分,每一个去到运动会的人都是参加活动的一份子。此外,比较深刻的还有,我跟美国的一个特奥运动员,她是游泳的特奥世界冠军,是我的搭档,我们一起在做一个游戏,我们需要去画一张对未来的设想,通过画这幅画,我们进行了很多的交流,思考未来生活是怎样的,比如我问她你未来要不要继续游泳啊,是不是要画一个游泳池在这上面,类似于这样。这样的游戏也是一个沟通的过程。我觉得这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后来,我还去了北京市宣武培智中心学校参加活动。我当时是去当特奥运动员的融合伙伴,和特奥运动员一起玩,一起做游戏。对于我来说,这是心灵的洗礼,因为你跟他们真的是将心比心,大家都坦诚相待,不用考虑其他的东西,不用考虑其他的压力,或者其他的社会问题。到了那儿,有点像回到童年一样,回到幼儿园那段最天真无邪的时光。
特奥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人,可以分两个群体。一个是特奥的从业人员,另外是特奥运动员。先说特奥的从业者吧,我印象深刻的是几位特奥东亚区的工作人员,他们能力都很强,可能一开始不是从事特奥工作,是在一些待遇很好的行业或者企业中任职,也有很丰富的经历,但是他们开始接触到特奥之后,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原来待遇比较好的职位,来到了特奥,并且真的是全身心地投入。
很多活动筹办时,他们人手上比较吃紧,随着特奥的推广,活动会越来越多,而项目的增加并不与人员的增加成正比。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工作非常紧张,压力也比较大,待遇也没有他们原来所从事的职业好。但是他们还是很努力、没有抱怨地去做这个工作,他们既是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也是活动的参与者、实施者,担任了多重角色,但却没有获得多重角色相应的待遇。他们都不是因为看重待遇而从事这份工作的,这种精神难能可贵。我对好几位特奥东亚区的工作人员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另外,我接触过一些特奥运动员,他们也知道自己与普通人有一些区别,但是他们非常自信、开朗、乐观,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开展过一个“拒绝侮辱性语言”的活动,活动意在让我们对一些污言秽语、歧视性的语言说不,活动中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特奥运动员的过往,知道一些运动员也有过被别人歧视、冷眼相待的经历,但是他们很开朗,能进行自我调节。他们既是特奥运动员,也参加过特奥组织的一些活动,担任志愿者服务其他特奥运动员。
我记得有一位女士参加我们组织的一个特奥活动,她自己曾经是特奥运动员,虽然年龄比较大了,但是她一直在从事与特奥相关的活动,参与服务,这也是很难能可贵的。她走路不太方便,一瘸一拐的,但是她仍然全程坚持,就算自己走得慢一点也不要别人帮忙,并且多次参加活动,她很坚强。
还有一点让我很感动,那就是他们很坚持。我不知道“坚持”这个词用得对不对,比如我们一起参加一些小游戏、小比赛,可能是一个接力跑的比赛,分很多组。一组可能有十个人。有些队要强一些,跑得很快,十个人转眼就跑完了。有的组可能要弱一些,里面一些组员跑得不是很快,甚至可能跑不了,需要走下来,他们的差距被拉得很大。比如说甲组已经跑完,乙组才跑了一半,剩下的五个人还是很认真很努力地像自己是第一名那样去跑,即使最后剩下他们一队人了,他们还是很努力地去跑。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表扬的。他们很坚持,不管自己是不是最后一名,他们很享受比赛和游戏的过程,就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完成。反观我们有些学生比赛接力跑,跑到后几名时就会有一点泄气,但是他们不会。他们即使跑到了后面,也会一个人跑完,最后大家一起拍手啊庆祝啊,我觉得这种氛围特别好,特奥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参与。
我认为,利用高校平台,可以更好地位特殊人群提供更好的服务,促进社会融合。第一,高校有较好与完整的体育设施,并有专业的体育教师,能够给特奥运动员提供良好的训练环境;第二,大学生是青年志愿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有效的宣传,能够招募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帮助与服务特殊人群;第三,高校与企业有良好的沟通,通过高校就业部门的联系,能帮助特殊人群寻找就业的机会,帮助他们走向社会;第四,各院系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特殊人群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医学专业可以提供医疗服务与健康咨询、法律专业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等等。
通过高校,相当于为特奥运动员搭建了一个与他人交往的平台。一方面,特奥运动员可以与其他人有更深入的接触,逐渐扩大特奥运动员的社会交往网络,促进社会融合。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参与这样的活动,能逐渐认识这些可爱的人,通过这些参与活动的学生的影响,可以改变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这些受影响的当中可能有人不会直接参与特奥,但通过了解特奥,会有助于他们消除社会对特奥运动员的偏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特奥运动员的可爱之处。
[1]鸡毛信: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军民在传递紧急情报的信封上粘附鸡毛,称为鸡毛信,以示十万火急。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同名电影,从此鸡毛信的故事家喻户晓。鸡毛信源于我国古代的 “羽檄”“羽书”,羽檄为军事文书,常用于征调军队,插上鸟羽表示情况紧急,必须迅速递送。
[2]“小白菜”是人们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的昵称。志愿者统一身着绿白色相间的服装,宛若一颗颗小白菜,青春活泼,热情服务。亦有一层意思指志愿者勤恳工作,还时不时受气,好比遭到委屈的“小白菜”。
[3] USC,南加州大学,当年世界特奥运动会的比赛场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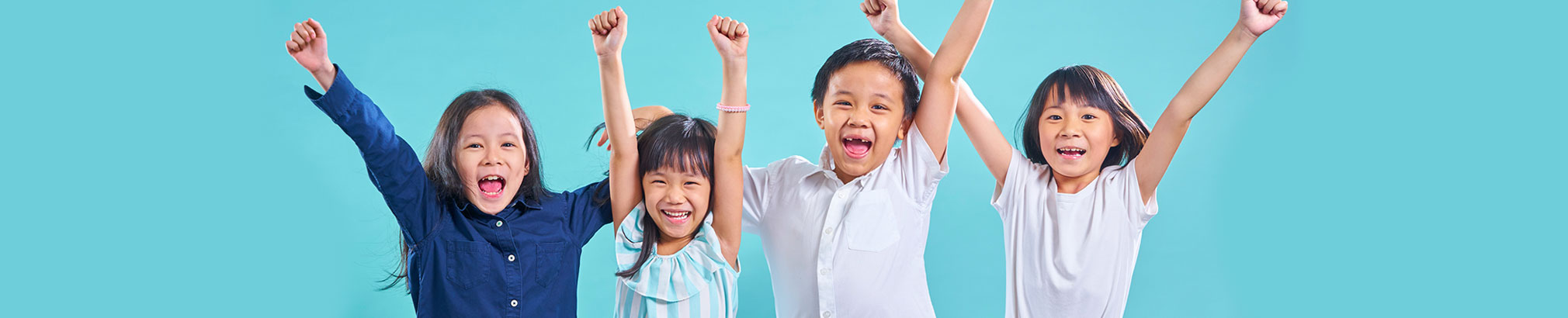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702007458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70200745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