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女,1967年生。北京市海淀区培智学校校长
我小学学习挺好的。现在想起来,我小学可能是一个多动的孩子。我现在搞特殊教育,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都有了解,我就老给自己贴标签。在我印象中,小学的时候老师总说我不守纪律,做小动作,还爱说话。我爸比较大岁数生的我,对我很宝贝。开完家长会,他回来说老师批评我不守纪律。但我爸问老师我学习怎么样,老师只要说学习好,那我犯的那些错就过去了,没关系了。所以我觉得家庭给了我一个很宽松的环境。
现在我搞特殊教育,我知道多动的孩子跟老师不理解孩子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上课举手发言,老师说你要会你就举手,你举手,我才叫你。当时我肯定是特别爱表现自己,而且我又会,所以我就举手。但是老师不一定就会叫我,那么多人举手,老师怎么会都叫得到。老师可能会叫那些不举手的孩子,或者叫一些他认为不太会的孩子,然后我就“咣咣”的使劲在那敲桌子,老师就认为我不守纪律,在捣乱。既然老师说会了就举手,孩子要表现就举手了,并没有直接冲撞规则,他就是要表达而已,就被认为捣乱。
多动的孩子,他就是爱动而已,甚至还很聪明,他们的创造性特强,联系能力很棒,就是本体感不足。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有的孩子来说,他手里必须捏着一个东西,他的注意力才能集中。你现在能听我说话,是因为注意力知道我在说话,你知道你自己在哪儿,你能把注意给我,即使你现在不动,你也知道你脚在哪,你屁股在哪。但是小孩,特别是多动的孩子,他动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身体在哪儿。现在一些孩子都有这么一个毛病,在做事情的时候要颤抖着,或者要捏着一个东西——其实这不是分散精力,反而是在集中注意力。如果他不动了,其实他的神儿是飘着的。
我爸爸喜欢女孩当老师,就让我去当老师了。正好海淀区、朝阳区都在招老师,为了家长心愿,自己的抗争精神也没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大,就去当老师了。想着如果一两年后,不想干了,也可以去干自己爱干的事,就这样一脚踏进了教师这个队伍。
我不是师范出来的,需要前期培训,半年培训之后,我们被分到学校已经11月份了。学校9月份开学,老师早早的都已经到位了。等我们11月份再来的时候,就是多的人,为以后储备的。学校就让我去学校里的辅读班了。辅读班就是给智障孩子开的班,那个班需要老师,老师不足。我就去了那里,开始接触特殊儿童了。那时还没有特殊教育学校。我从第一天当老师开始,接触的就是智障孩子。其实,我并不是想持续地当老师,后来真的是孩子和家长感动了我,留下了我。一辈子我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
有很多事感动了我。我11月份才进学校,没多久就放寒假了,就在家里歇着。突然有一天,北京还下着大雪,有一个小孩敲我们家门——白白胖胖的,手里还提溜着水果。我不记得他是拿了俩苹果,还是一个苹果一个梨了,就嘿嘿嘿傻笑着看着我。我当时特惊讶,因为是我的学生嘛,我知道他们家住得挺远的。我们家在阳光店军博这边,他们家在中关村那边。现在觉得很近,但是那时候只有一条路,也只有一趟车。我也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他我们家的门牌号码,我们家住哪。他就跟从天而降似的,对着我呵呵笑着,看着我。他进来后,在屋里转了一圈,看着我高兴,不一会儿就走了。可以读懂他的人就特别感动,他是放假了见不着老师,在家里也没什么人跟他玩,在学校还有同学老师跟他玩会儿,回家就只能憋着了。他知道过年要走亲访友,他就转悠着看老师来了,我特感动。
接触了智障孩子一两年多,我特理解他们,包括家长。后来其他家长也跟我交流了很多,他们生完这些孩子,有多么不容易。你的出现就像他们大救星似的,能得到这种特真挚的崇拜感,家长发自内心地感谢你,孩子也是发自内心地喜欢你,就会有很多职业自豪感,我觉得是赢得了社会赞誉吧。最后,我感到做老师也挺好的,能帮助他们。
那时候培智教育在我们这里是刚刚起步,走的每一步都是困难。比如说没有教材。开始教的是普通学校的教材,不会也使劲教。5以内的加减法,我可能教了四五年,孩子还是学不会,我跟孩子发脾气。孩子写不出来字儿,我也着急。像平常在黑板上画一个三角形或画一个角,学生根本不明白,就需要用东西——例如纸壳,剪出一个能动的角,让他们去摸,去感受这是一个角。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做感知课。特殊教育给我的感觉是,我们不怕困难,因为我们所有的目的就是在解决困难,读懂孩子。
从1988年到1994年教过一轮后,我觉得我们在浪费青春,教的东西,他们永远学不会,或者是进入社会后一点用都没有。课程需要改革,需要研究一套适合他们的课程。1994年,我们了解到美国智力残疾协会(AAMR)每年都会公布残疾的定义,我们就从它的定义里发展出来了一套功能性课程的量表。
我们不教纯属知识类的东西,转化成功能性质的内容,例如教他买票乘坐地铁,数学是运用在生活当中的。首先孩子上课的时候不乱跑乱闹了,因为他听得懂老师在讲什么了,这些课程更多在于操作,更加有趣,更有吸引力。我们做活动性课程的时候,孩子都能参与。他会的东西多了,智能也开发出来了,所以效果特好。没到一轮,全国都开始学习我们的课程了。那时候特教也开始在各地发展起来,大家都互相学习,一下发现我们这个思路是对的,就应该这么改,后来全国很多的地方就开始做我们的这种个别化教育。现在北京市,甚至全国都在做个别教育计划。
这一路走来,我做了很多改革,认真进行了很多研究——既然你想教育他们,想把特教当成一个职业,就不能被人看不起!很多人特别容易把你当成看傻孩子的——你们没什么本事,你们教不了知识,就只能看傻孩子,就这样被歧视了。后来我想,我必须有专业,我必须要能做康复,必须让大家看到我们有专业的力量,所以一路做科研,做课程改革,做康复,就这样一下子在全国就有名了,我也是全国智力障碍协会的主任。
到现在,我在特教这个圈子里工作时间是最长的。全国在内,一定没有比我工作时间长的。刚来的时候,都是退休的老太太、老教师在做,我是最年轻的。到了专业的特教学校之后,我也是年轻的。那些老教师早就退休了,我一直持续地在做,坚持时间也是最长的。
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我这一辈子就认真完成了这么一个使命,可以说是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不忘初心,从我进到特殊教育,就留下了我的初心,为这些孩子造福,让这些苦难的孩子有幸福感和尊严。30年以后,干的仍然是这个事儿;不辱使命呢,我觉得老天爷塑造我,就是为一大事来,就是培智教育。中国的培智教育从无到有,我付出了。从无到有的阶段我赶上了,我推动了,我发展了,这就是我的使命,这个事情也是极其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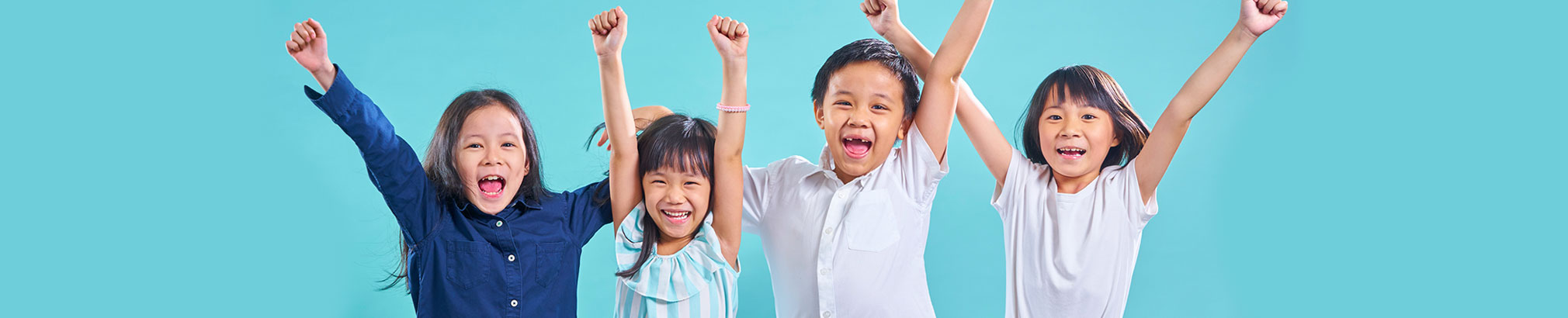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702007458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70200745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