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楠,女,1979年出生。黑龙江哈尔滨冰上飞扬运动俱乐部教练。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取得了市速度滑冰比赛的冠军。十三岁上的初中,在一个体校,班上有二十多个同学,都是练不同项目的,哈尔滨本地的很少。初中之后就上了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学校,之后又上了体育大学,做了专业运动员,每天的任务就是训练。得过全国单项赛的冠军,省比赛、市比赛什么的冠军都得过。
2001年,我刚上班的时候,就带了8个孩子去美国,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特奥会,也是那次特奥会使我坚定了要做特奥这件事。
那一次比赛把我自己震惊了,是我职业生涯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我小时候听说过特奥会,我十三四岁,训练的时候看到当时有这样的孩子在训练。再往后分配到单位,领导说你是专业滑冰的,刚刚好我们有运动员被选上去参加这个比赛,当时他们还不会滑冰,让我去带他们训练。当时我认为滑冰应该是我们当年的那种样子,不了解特奥运动员,那段时间教他们滑冰还是挺折磨的。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也是硬着头皮去美国比赛了,当时对特奥会的规则也不熟悉,但那次比赛的成绩还行。那次比赛把我的内心给打开了,这个事情原来可以这样做。当时在训练中遇到很多困难,我认为特殊的孩子能学会滑冰,但是他却不会滑得太好,等真正到赛场的时候,我就看到,比如说加拿大和美国的孩子滑得特别特别好,当时就觉得:是这样吗?特殊的孩子也能滑得这样好吗?当时我就认同了一句话: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我发现,原来问题出在我这,肯定还是方法、时间还有沟通可能没有做到。从美国回来后,我就在我们学校,选了第一拨孩子,当时有三十几个人,从3、4月份开始练,一直到11月份。那时候练轮滑,因为轮滑和滑冰特别像,而且夏季特奥会有轮滑项目,这样我们也可以参加夏季特奥会。就哈尔滨来说,还是以冰为主,11月份的时候,天也比较冷了,我们就带孩子去滑冰,经过这一夏天的轮滑训练,他们第一次上冰。
教他们真的很痛苦,有的一个小时才能在冰上走一圈,也只能在冰上走,不能滑。滑冰是一个技巧性项目,冰很滑,冰刀又很窄,它不像你穿的鞋,普通人学滑冰都会有一点害怕,都要克服恐惧的心理,那特殊的孩子会把这种恐惧放大很多倍,他们特别特别害怕。我记得有一个孩子,每往前迈一步大约有5公分,下一只脚迈出去的同时又退回来两公分,一圈大约有200米,一个小时只能走一圈。这样训练了一个夏天,三十个孩子最后上冰的也只有八个人。
家长也是看在我这份热情上,相信我,跟随着我们,带孩子去冰场。那时候真的很苦,哈尔滨的冬天大约在零下二十几度,每天晚上下冰在八点多,然后坐公交回家。早上要在上学之前训练,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多好多天。家长也是在最初没看到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无条件支持配合,真的非常感谢家长。
在冰场上有一个特点,教普通孩子滑冰从滑冰开始教,教特殊的孩子要从系鞋带开始,他们不会系鞋带,滑冰鞋的鞋带又比较麻烦。那一天我把所有孩子的鞋带系好之后,他们站在冰场上,我在系我的鞋带的时候,能听到所有家长说的话,“我的儿子会滑”“我姑娘也会滑”,当时我还没有看到,家长说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当我站起来,看到他们滑冰的样子,虽然滑得不是特别规范,真是特别特别开心,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人生当中最开心的一件事,这一场训练很快就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就一直在笑,止不住地笑。
下了冰之后坐公交车回家,实际上在中途要换一个车,我在太平桥坐104路换83路公交车。那天我从104路公交车下车就特别兴奋,有车也没有坐,一直往家里走,大概走了二十多分钟,走的路上就一直在给之前残联的领导和同事打电话,说我成功了。回家后,洗漱完,发现脸特别特别酸,是一直在笑的缘故。从那之后,虽然面对很多困难,也都顺利克服了,一直走到了现在。我们有脑瘫的孩子,走路非常不协调,通过滑冰的训练,肢体协调明显改善了。
特奥运动员,最初的时候,我会选身体比例相对好一点的,不要太胖也不能太瘦,跑步相对协调一点儿的。你们可能不理解这有什么难的,普通孩子走路跑步协调能力都没什么难的,但特殊孩子不用说特别协调,就是相对协调的都很少。
随着参加比赛越来越多,我对特奥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之后,这个队伍也相对扩大了,主动来找我要参加训练的也就越来越多。原则上说,只要不是能力特别差,从事这个运动的时候有过高的安全风险的话,我们都会要。希望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得到锻炼。
前一两批运动员会认为我是一个太严厉的教练,很害怕,很严格。最近新来的一些孩子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招人喜欢的老师。现在没有之前强调纪律性,以前就是一定要取得成绩,一定要滑得够快。现在更多强调的是兴趣、参与,然后和来训练的孩子们相互融合,孩子与孩子之间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家长叙述自己的苦闷……很多方面吧。当然我们还是会在比赛中做到最好。相对而言,除了比赛,现在我还会在比赛中带他们玩,玩得很开心。
大概2009年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一次又一次参加比赛,周而复始下去,孩子只是在特奥运动训练过程中,在适应比赛过程中得到了锻炼。随着第一批孩子的年龄越来越大,可能就不再参加特奥会了,我们会把更多的机会给需要锻炼的小年龄段的孩子。那么这些年龄大的孩子,走上社会以后需要做什么事?在2010年左右,我们开始考虑这些孩子怎么能够通过特奥的锻炼,改变后续的生存状态。
当然,我一个人的能力比较小,只要是特奥会运动员或是有特殊情况的孩子愿意来训练,我们都欢迎,哪怕他不能参加比赛,达不到参加比赛的能力。一些老运动员,比如说小王,他从2000年开始就训练,现在也还在我们这个队里训练。这个过程中,他是特奥大使,2007年上海特奥会的时候他是旗手,在第四届全国特奥会的时候,哈尔滨是东道主,他在闭幕式上做了演出,也算是一个明星特奥运动员。他现在依然参加训练,参不参加特奥会,反而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会上的一个生存状态,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环境。
他们可能每天和家长在家里,每天都坐在床上。小王还是比较活跃的,有些严重的孩子,用父母的话来讲,可能会一直坐在家里的一个位置一动不动,甚至把家里的皮沙发坐出一个坑,他都不会挪一个地方。他们就需要一个环境,比如说每周三次,可以到训练的环境中来,跟朋友、同学见个面。
小王现在应该三十岁了,三十年来他已经接受或者认可了现实,但是他内心当中还是有一些苦闷,或者是不被外人所能理解的情绪,需要跟家长来沟通。所以,从六七年之前,我们这支队伍的训练,已经不完完全全是为了参加比赛取得好成绩,更多是充当了一个家庭或者特奥运动员的精神交流的出口。几天见一次面,同学们、朋友们互相之间有一个交流,他们会认为这件事情——每周训练三次——是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期待。
当他们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后,通过我的能力能做到的就是,我们冰场现在有三十几个工作人员,其中安置了四个特奥运动员做服务专业,他们在这里工作,跟其他人员是同工同酬的。其中有两个轻度的孩子,我们的同事并不知道他们曾经是特奥运动员。
社会整体的宣传还是比多年前要好很多,但我觉得还不够,平时的关注比较少。媒体在你比完赛回来,报道的比较多。另外就是,全国助残日、国际残疾人日、世界自闭症日、唐氏综合征日,这种比较特殊的日子,媒体会有一些报道。提高社会各界的关注的话,还是要发动周边社区的人对这些孩子多加关注。
国际比赛可能参加的人比较少,国内的特奥比赛、培训、各种活动比较少。我比较幸运,参加国际比赛的次数比较多,参加的活动比较多。我更希望像我这样的教练员,这样的孩子能得到更多的机会和锻炼。
如果训练完之后,连参加比赛的机会也没有,孩子没有展示的机会,教练也没有动力,家长也不知道,我练这玩意儿干什么……还是从管理层上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教练干着他有劲儿,有个比赛就好比学习有个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有个阶段性的成果验收。
从中国特奥会层面,希望多一些活动,多一些培训,可以是竞赛、夏令营,或者是教练员的培训、交流。我觉得活动嘛,要动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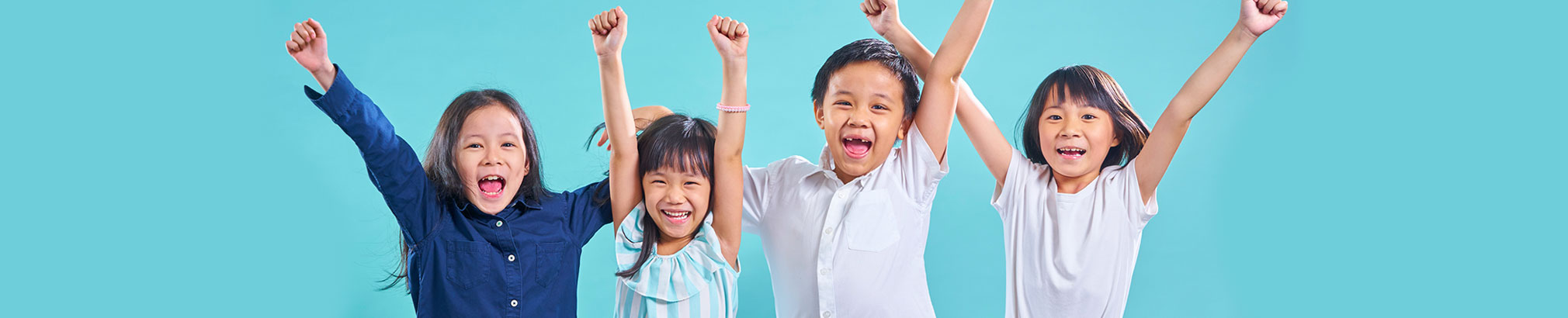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702007458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702007458号